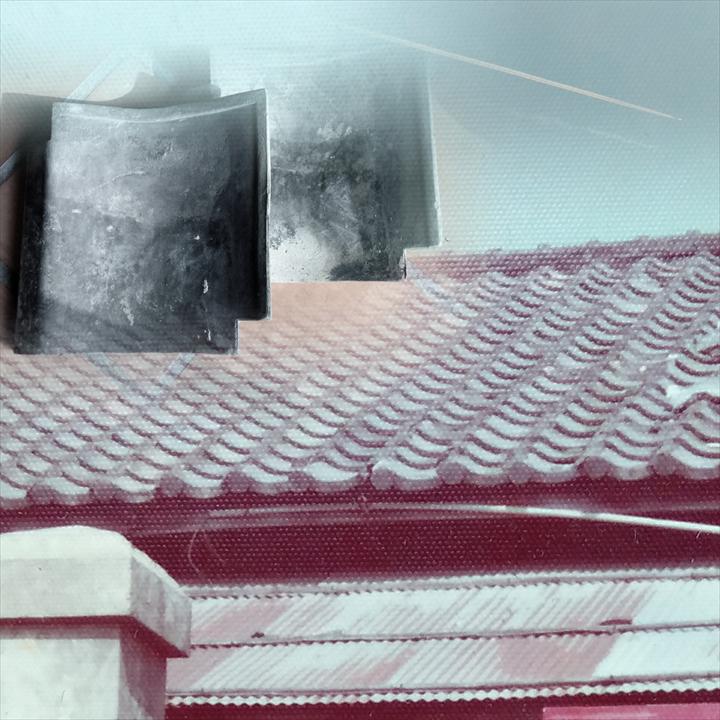
黑瓦之下
圖文/ 姚克洪
屋旁龍眼樹。午後溫暖的陽光在扶疏的樹幹枝枒中陰影交錯。延伸的樹幹斜向屋頂。我小心翼翼的攀爬過去,小心的把腳垂踏上屋瓦…一個所有鄰居都在午覺,蟲鳥都在午覺,母雞和小雞午覺,貓捲窩在屋角也在午覺的時分。屋瓦很溫暖,有點燙。我輕輕地一點一點四腳往上移動,就這樣騎坐屋脊上。
藍天白雲,周圍都是日式黑瓦的屋宇,整整齊齊的雙拼宿舍群,簇擁在以七里香樹籬,我阿爸上班的事務所周圍。更遠就是廣闊的甘蔗田和錯落的民房。喔,有麻雀們隨著甘蔗葉起伏的風浪,在細絲般電線間飛飛落落。空中西方一條垂直上升的飛機雲。緊跟著那微小閃爍的亮點持續上升的線條乾淨而銳利,下方就逐漸的膨脹開來成一抹帶狀白。更下方的遠方是橫開來的積捲雲…我的布袋戲在那裏滾動,幕幕開演…我的小西園,我的伍洲園。我的大俠一江山。

離巢飛行式
2002年,這棟母親住了五十多年的房屋,這棟我振翅離巢起飛的窩,這一片日式宿舍群來到面臨拆除的時刻。失魂的母親終究不得不北上跟我了。搬運的卡車啟動前,我請幫忙搬家的朋友拆下兩片黑瓦…就是這二片。

黑瓦正面

黑瓦背面
我不了解黑瓦是如何燒製的。少女時期的母親在祖父經營的磚ㄚ窯做磚,給陶工煮食,煮半暝糖粥,也不知道黑瓦是如何燒的。那座磚窯廠在祖父過世後被花天酒地的兒子賣掉…聽我娘說土地很大,有採土遺留下來的池塘,養著魚和鴨鵝。傳統做磚用的工具是厚實的木模。即使當年已經有機器製磚設備,但限於電力共應,磚窯場生產的依然是傳統手工紅磚,煙筒灶磚,油面磚…。工人把濕泥大力摔入木模中,用細繩刮除餘土,敲抖出來的土磚要用一片叫做GaU-AR的木片整修。被稱為油面磚的高級品,要在磚土逐步乾燥的過程數度抹水,並以GaU-AR
整修過。陶工逐一整修每塊土磚,發出劈啪有節奏的聲響。乾燥的油面磚土塊進窯時表面已被修抹的光潔密實,並排在火度最平均的窯位。油面磚是重要的建築鋪面呈紅或紅褐色。即使是被稱為火頭磚,因高溫變形,顏色變深。也不是黑瓦的深灰黑色。
長大後才聽得黑瓦的燒製是使用一種水煙法。燒製溫度與一般紅磚的溫度類似。窯工以目視法看火色判窯溫。攝氏800度火色正紅色,隨溫度上升從正紅轉橘紅、黃,黃白乃至青黃,青白。紅磚燒製的溫度落在攝氏1000度上下,火色在正紅與紅黃之間。判定窯火溫度不難,難在如何從火孔判斷及調整使各窯位的溫度相近。當溫度到達火紅後,需要在高溫時從火室塞入潮濕的薪柴並潑水後封窯,造成不完全燃燒的大量黑煙。這正是有別於一般紅磚燒製的特殊燒製法。富含二氧化碳碳素的黑煙被瓦片大量吸收,形成密實的結構和深灰黑的顯色,在無形中給予溫度沒有達到磁化的黑瓦增加了強度和密度,正好強化作為屋頂材必要之防止日曬膨脹龜裂,防水的滲透效果。可惜,我終究無緣目睹此燒製的實況。
外出經商買賣中藥材逃避阿本仔徵兵、浪跡中國東北、上海、海南島,沖繩,練得一口流利標準北京話的父親在戰後得以覓得一份公務員職務…建立了他漂浪半生的家,也給了我懂事後,一張植入深深腦海中,鮮明記憶卻遍尋不得的全家福照片。那是終戰後數年,非全員到齊,不經意之下的全家福照。憔悴,依然年輕的母親和她懷中的我。綁小腳的祖母。一身白淨衣服的父親…照片裡人物各有表情心思。年幼早熟沉默的大哥,單純快樂的養女二姊。是偶然?或也許是一種虧欠感?父親在事務所附近的市場開了一家名為協豐商號的小陶瓷店。有一搭沒一搭的開了幾年,算是對變賣祖父一手建立的窯場的致歉行為?

這種說不出口的虧欠,也反映在他為母親種植一片百合花上。
可惜,心底內的距離已經太疲倦了,再也沒有眷戀,沒有仰望了…晚年中風的父親對著照顧他的妻子,終於由內說出對不起這三個字,並表示下輩子由他生成女人來服侍她。母親的回應是…下輩子?喔,偶不認識你,你不認識偶!…黑瓦之下,這時間礦脈裡,一粒看不見終將隕沒,溶忘的微小結晶。